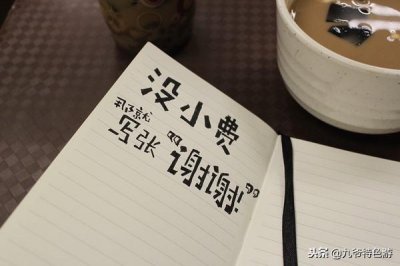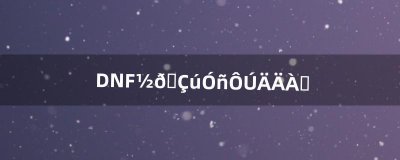冯双白:艺术容不得半点虚假

冯双白近照 本报记者 郭红松摄/光明图片
【走近文艺家】
5月22日,舞剧《刘三姐》进京演出,并将开启全国巡演之旅。该剧编剧、65岁的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准备创作一部关于朱自清的舞剧,正处于一种酝酿期特有的痛苦状态中,努力寻找着一种适合朱自清的舞台形式。
对于许多文艺创作者而言,每一个创作的前夕,仿佛能量在极度收缩,汇成一个高密度的点,然后是膨胀和释放。当最后一个字落笔,这种能量一泻千里,然后是放空,等待再一次收缩。冯双白或许就如此。在《刘三姐》上演的前几天,当记者和他谈及该剧时,他已记不清这是自己创作的第几部舞蹈作品了。“至少二三十部了吧。”他说。
冯双白喜欢创作。20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舞蹈作品——一部关于渔民生活的舞蹈诗。渔民在广西被称为“咕哩”,方言里“臭苦力”的意思。冯双白反其意而用之,要在舞台上告诉大家“咕哩美”。不过,他在广西北海待了一个月,毫无头绪。
一天夜里,台风大作。冯双白和总导演邓锐斌来到海边,漆黑一片,不见五指,暴雨和狂风打在身上,巨浪带着咆哮。两人恐惧不已,赶紧往回走。一转身,看见远处岸边,漆黑中亮着一盏灯。冯双白脱口而出:“有了。”
于是,“灯”成了大型舞蹈诗《咕哩美》的第一个意象和线索。“灯”,是渔夫和渔娘家里的灯,是渔夫出海时渔娘交到他手中的灯,是暴风雨中挂在桅杆上象征光明的灯,是穿过暴风雨回到家的指路明灯。“灯”亮了,这部舞蹈诗剩下的部分也就清晰了。第二部分主题是“网”,以渔网为连接,勾连起海边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一部分是“帆”,以挂帆、扬帆、万帆齐发等,观照时代。
1997年,《咕哩美》首演,一直演到今天,依然很受欢迎。暴风雨中的那盏灯,为《咕哩美》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冯双白后来的艺术之路指明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深入生活,做到“心入”“情入”。“我的灵感完全从生活中来。”他说。
冯双白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不止。或在笔尖,或在脚下。有时候烦躁不安,有时候恍然大悟。
在创作舞剧《风中少林》前,冯双白对武术的想象是打打杀杀。20多次上少林寺、与僧人一起生活后,才发现自己全错了。对于那些少林武僧来说,禅是对生命境界的体悟,武也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修炼。于是,整个舞剧的走向都变了,深入挖掘少林文化的深厚传统,表现禅、武、医三位一体的融合,从出尘忘世里寻找积极入世的少林文化精神,“以前的设想就是打,现在是对少林文化本质的探索,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的体现”。
50多年前,正在北京景山学校上小学三年级的冯双白,不会想到他未来的舞蹈世界是这样。那时,一位老师偶然看到冯双白耍大刀,问他想不想到少年宫学舞蹈?“学舞蹈做什么?”“你要是学舞蹈,可以天天玩大刀。”冯双白就这样“拐进”了舞蹈世界。
1974年,冯双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文学和文艺理论,这是他另一个向往的世界。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招收首届舞蹈史论硕士,冯双白追随到此。这个曾经为了一套雨果的《悲惨世界》而夜行40里地的青年,找到了文学和舞蹈的连接点。
艺术理论的学习和多年的演出实践,合二为一,冯双白从一个舞蹈表演者,转向舞蹈理论研究者,又从研究者转向创作者。这时,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身体语言。与文字语言不一样,身体语言可以把内心与形式完美地统一在一起。身体语言看上去很难直接翻译出来,但很容易给人带来感染。这正是让冯双白着迷的地方。
所以,当舞蹈与文学相遇,冯双白做起了舞蹈编剧。“芭蕾舞、古典舞、现代舞、民间舞、民族舞……每一个舞种的身体语言都有独特的规律。我们根据规律,尝试通过身体语言来讲述人类文明的故事和情感世界。”他说。
近年来,舞蹈创作的繁荣推动了舞蹈语言的探索和突破。但冯双白注意到,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不足,很多舞蹈作品的艺术形象千人一面,一味追求视觉上的“美”和“漂亮”。有的作品制作很豪华,但没有情感支撑点,“情不够,舞来凑”。“靠堆砌人,堆五六层,甚至十几层高,相机都拍不了,要动用无人机在空中才能拍到。”
冯双白将之归因于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现在电脑上随便一搜,什么资料都有,但资料里的东西毕竟跟实际体验不一样。”实际上,冯双白本人的创作经历很好地诠释了生活之于艺术的意义,但他坚持还要用一段他人的经历来进一步提醒舞蹈界的创作者们:
有一次他们经过藏区,遇到一位背着青稞的藏族妇女。原来其时正是“望果节”,当地女人都把经书背在身上,还用青稞来装饰。一位同伴在那瞬间闻到了青稞特有的味道,并触碰了青稞的芒刺。这味觉与触觉带来的冲击,久久不去,激发她创作了一个关于青稞的优秀舞蹈作品。“如果你在电脑里找青稞,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冯双白说。
或许是自己都被这个故事打动了,或许是再次回想起了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的创作之路,冯双白颇为感慨:“还是要老老实实创作,乖乖地深入生活,到生活的底层去,容不得半点虚假。”
“没有生活是不行的。”冯双白忠告。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9-05/22/nw.D110000gmrb_20190522_2-13.htm
从舞蹈表演者,转向舞蹈理论研究者,又从研究者转向创作者。芭蕾舞、古典舞、现代舞、民间舞、民族舞……他尝试通过身体语言来讲故事。回想自己二十多年的创作之路,他说,“没有生活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