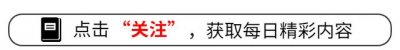喔,嫩江湾,那一滩童趣之鸟趣
作者|未央君
打鸟,儿时又一乐趣。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啥呀?谁跟谁呀?那个时代,小孩子散养、释放天性的时候,哪懂这个啊!
打鸟的乐趣不分季节,春夏秋冬,五彩缤纷。打鸟应该是打雀,也不对,是打雀,读qiao。写起来,打鸟看着顺眼。
春天鸟的种类多,打鸟的地点也多,收获的快乐也轻松。
春天打鸟夹子的诱饵就一样,就是玉米螟,俗称桨杆虫,苞米杆子苞米茬子里多的是,活的,鸟儿最爱。系在夹子上,露在土面上,蠕动,引诱鬼子来打枪,不对,引诱鸟儿来叨,一保一个准。

在树林子里打,依体型从小到大的有柳树叶子、呱嗒板子、蓝颏、花碗碴、红颏、三道门、青头楞、率叽,在壕沟地边打有麻渣、额赖、牛尾巴黄,介于树带和地边的有胡巴喇。胡巴拉,似乎是隼类,凶残,另类,生命力强,好象爱钻坟圈子,一般不专门打它。它主动找死,就当搂菜柴火捡兔子,当捎带了。
在水边打,上面的鸟部分也有交集,但更多的是黄豆瓣、红马料,还有水禽水鸡子,小鸿雁等等。
在水中打,对,水中,打那种通体雪白,身形俊俏,经常悬在空中,紧盯水面,忽地一个俯冲,扎入水中,再跃出水面,嘴里就叼起一条小鱼或水虫的鸟,学名应该叫江鸥的,但我们只知道它叫打鱼榔头,因为印象中它就吃鱼,打起来难度系数8.8吧。但我们照样对它们下家伙什。就是使大夹子,用麦穗鱼或小白漂子做饵,夹子支在江水将能没人蹄的浅水区,鱼饵和水面一平或隐在水下一扁韭菜叶,微风微浪,小鱼似动非动,然后人就岸上等待,运气好的,一盘夹子一晌午也能打两三个,味道嘛,忘了,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只是我能叫出名和能想起来的鸟,有些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些被忘记了。但是有这些鸟是肯定的,我叫的这些鸟都不是学名,都是俗称或绰号,或者象我们翻译外国人的名字,不是直译就是意译,都不很准。比如额赖,我们也叫鹅赖,现在城市里养鸟的有这种鸟,分黑黄两种,能哨出很多套叫声,学名应该叫叫天子百灵鸟什么的。它叫得好听,清脆婉转,但窝却及其简陋,就在马蹄窝子牛脚印子里,或一颗车轱辘菜(车前子)一簇蛤蟆腿叶下,委吧委吧简单铺点草叶就是个窝。一次七八个蛋,一窝七八个崽,有的人找到鸟窝也不动,专门等幼雏要出窝时来抓,估计就是卖给城里人了。还有呱嗒板子,应该是柳莺或苇莺,能学十余种鸟叫,窝悬在芦苇杆和蒿子杆上,编织的很精致。现在南湖苇丛里叽里呱啦叫连声的就是,什么时候听着都有一种亲切感。
我的打鸟高光记忆是一次打了一百大多,半土篮子。那天大人支持,都在种园子呢,妈妈上邻居家给我借的50多盘夹子,我就挎上土篮子一个人去了东江,找到一个江叉子里的一个大车店三连铺炕大的狭长水泡,沿泡边支夹子,夹子支在离水边一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喝水的鸟能看到食饵,50 多个夹子围住了水坑的大半边,可是没有鸟来。看泡子里水动,感觉是有鱼,顾不得水扎骨的凉,下水就摸到两个老头鱼,这种鱼当时是没人吃的,都是鸭食。现在知道是河豚的一种,价格还飙上来了。
当时想法打不着雀就用它充数吧,好歹是收获。说话间,天要晌午头了,就听啾啾的开始上鸟,就听啪啪的,鸟开始叨夹子了。原来,一上午鸟在野地里觅食,这会儿口渴了,开始来喝水了。我的天,这鸟这么多,我掐一头顺泡子沿溜夹子,十分八分钟一次,每次都十只八只的。摘下鸟,销上虫,埋好夹子,然后进行下一个、下一个,个个都是褐背黄肚皮的黄豆瓣,通身黑紫的红马料,间或麻炸、额懒,都是个大体肥的上等雀,我都有点忙乎不过来了。晌午头一过,鸟不来了,我也饿了,连夹子带雀整整一筐,我凯旋了——现在想想有些后怕,东江野外,就我一个人一上午,真是的!——不过,大人忙了一下午,褪毛去内脏后的鸟,油炸,焦黄酥脆油香,那滋味,现在成了绝唱。

按节气说,小满雀来全。应节气,雀来全,就打不到了,鸟们分散开行动,都忙着恋爱繁衍后代去了。这时可以捡鸟蛋了,野鸡野鸭大雁蛋。一撮毛哪里,看鱼窝棚的把式都成挑子往家挑各种禽蛋,当然也有丹顶鹤的蛋,那时没有保护一说。“打猎是有规矩的”,一次二嘎子,张晓军,我们三个玩得来的小伙伴去捡野鸭蛋,二嘎子给我们讲规矩:“捡到东西人人有份”。他强调“大人都是这样的”。说得我和张晓军信了,我们刚上一个漫岗子上,在一缕倒伏的小叶樟中,嘎嘎嘎—--飞起一只麻头鸭,二嘎子近水楼台,紧跑几步,扑到鸭窝上,护住鸭蛋,蹬蹬小短腿哭叫着“我的我的,我看见的,都是我的”,好象谁和他抢了似的。起身,大襟上沾了块鸭蛋黄子,直往下淌汤,我和张晓军都没笑。
冬天打雀,兴趣也是满满的。冬天鸟类品种比较单调。野外就是雪雀和苏雀儿。大型的野鸡和沙斑鸠(也有叫白了叫仨半斤儿的,意思是三个半斤,其实是俗称飞龙的,一个就半斤左右),小孩是打不着的,我们只能打打雪雀和苏雀儿,还有老家屁(留鸟,在屋檐子筑窝的家雀)。
冬季雪后,最好是无风后的小雪,一两寸厚,有山盖山,有坡漫坡,无山无坡,弥漫原野,松软似棉,平整如镜。三五个小伙伴,留在雪地上三五行直直的清晰的小脚印,直奔村后那片谷地。咵咵,几脚踢出大约脸盆大小的黑土地,支上一盘夹子,这季节夹子上的诱饵是谷穗子瓣,黄黄的,在黑白分明的夹窝子里很抢眼。冬天土都冻住了,好在雪雀饥饿,趋食性强,夹子只要把底部埋上露出诱饵就行。每人三五盘,十来盘的。迅速支好,马上撤离。躲在百十米外嬉笑打闹,等着雪雀来临。
不知多少时间,几十分钟,个把小时,一两个钟头,反正运气主宰,赫然间,悠悠的成群的雪雀忽高忽低忽东忽西打着旋从东南西北各个方位均可扑面而来,那十几几十个夹窝子就像大地这篇白纸上的几点墨珠,黑白分明,格外抢眼,不要说有食物,就是嘛嘛没有,雪雀也要落地歇歇脚。于是鸟们急速俯冲奔向那些黑洞,又急速起飞再上蓝天——它们嘴快的同伙已经叨犯了夹子,为食而亡。小伙伴们几乎在鸟群飞临夹窝子上方时就启动脚步,因为经验告诉他们饥饿难耐加上飞行疲劳的鸟们不会放过这些明摆着的死亡,果不其然,几乎各个夹子都有收获,点高的,一夹两鸟,鸟为争食双亡。
最省心落意的是抓苏雀。苏雀一般都用滚笼,就是用秫秸扎的鸟笼子,笼子是分层次的,两边是机关,或者是滚轮,或者是夹拍。中间专设一室,放一个善于鸣叫的苏雀,叫雀油子,将笼子挂于室外的高处,每当空中有苏雀经过,雀油子声嘶力竭地呼叫同类,飞鸟不知就里,寻声来到,看见滚轮或夹拍上的诱饵,就是谷穗瓣,刚欲啄食,或顶头被拍入笼中,或失足掉入陷阱。所不同的是夹拍一次就能拍一只,滚笼则可当即复原,重复作业,效率很高。这实质是居家抓雀,不累不冷,而且每只都是活的。

现在世事变迁,从麻雀是四害,举全民之力赶尽杀绝之,到视为自然一分子,生杀予夺由人任之,到现代文明,人类立法保护之,是人对自然认知的主观改变。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这是古人处于人本善的本能劝告。可是人自以为是自然的主宰,对自然任意而为,过了度,于是有了矫枉过正的保护。还是在我的老家,嫩江边的那个地方,十多年前,一对年轻的肖氏兄弟,靠江吃江,用拌过药的小鱼和玉米粒,撒在江叉子水边,药些迁徙的麻鸭飞禽啥的,不料被举报,一查他们竟夺去了比丹顶鹤还珍稀的白鹤的命,且整整17只。按法条一扣,哥俩都失去了11年的人身自由。
当年法庭在当地开的现场庭,我跟着观摩,亲眼目睹我的淳朴的乡亲们,惊掉了一地下巴:怎么,鸟比人贵?!唉,法律无情,“欲射一马,误射一獐”,后果很严重。不过野生动物保护到现在,据说有的有的省考虑给野猪解禁,这家伙泛滥成灾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呵呵,风水轮流转,堂前燕成落配鸡。不远的将来,娃娃们可能有限度地体会我们当年打雀的鸟趣?内心真的期待。
敲打这篇文字时,杭州这里的留雀、象家乡“老家屁儿”一样在楼外雨棚缝管道孔墙角里筑巢的白眉雀在院内逛来逛去,几次撂笔细端详。几年前在老家楼前杨树上,看小巧的柳树叶子鸟在树叶间翻飞,有了文兴,成篇《且饮一壶春》。当下,这个小院,即时即景,教孙孙“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因为戏蝶娇莺就在此处同框---鸟趣得以升华,已不仅仅停留在儿时舌尖上的美味了。

作者简介:
未央君:本名王伟明,吉林镇赉人。机关文字工作者,现代作家协会会员。曾有通讯、杂文、随笔见诸《人民公安报》《检察日报》《法制日报》《保密工作》及《吉林日报》《检察风云》等报刊。近年来小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篇刊发西散南国文学、南国红豆诗刊、《作家文学》《作家故事》《中国现代文化报》《嫩江文学》《卡伦湖文学》等网络平台和纸媒,间有获奖。有两篇游记被收录《中国作家库》优秀作品展。